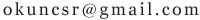汉语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先秦文学的书面语与其时代的口语是基本一致的,因此论语虽在我们现在看来很难理解,但在那个时候却是口语,因为这本身就是一本语录,不可能用太多书面语,而实际上当时书面语和口语并没有真正分开,人们还没有什么书面语的意识
为什么后来出现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分野,关键在于后来人对先秦文章的崇拜,秦汉以后的人们由于这种崇拜纷纷模仿先秦语言,在书面上仿照先秦样式,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口语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词汇和语法的变化都很多,可熟面上却被人们刻意的保持下来,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当然古人对先秦汉语的模仿并不到家,他们只能摹仿一些固定成语,如未之有也、何如、如之何、何有、……之谓也等等,在一些细微的词汇上却经常露出马脚,而这些就是我们研究各个时代书面汉语不同之处的依据
例如:尚书里的禹贡一篇,表面上说写的是夏禹留下来的文字,但其中的词汇完全是战国时代的语言特点,因此我们断定其为伪作
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栋梁,加之古代中国的教育并不普及,因此文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就更喜欢把文章写的生涩难懂,渐渐与当时的口语分离
这种现象一直到二十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时才得以停止
可是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白话文学并没有因为古文的生涩难懂而停止下来,从南北朝到明清都有表现,以明清的章回小说为例,最开始的三国演义还比较保守,并没有用白话,而是浅显的文言,水浒传开始就已经用白话文写作了,这些白话文作品体现了当时的口语,可谓别具一格
白居易的诗虽然老妪能够看懂,但绝不是平白的白话,否则便不能称作诗,诗歌是需要诗人的艺术加工的,丰富的修辞,生动的意象都是诗歌必不可少的要素,白居易的诗歌语言虽然老妪能解,但也不可能是完全的白话
中国近代的著名诗人黄遵宪讲究我手写我口,讲究形式上的浅显易懂,可以说是白居易第二
关于白话文学请参考胡适的著作《白话文学史》
现在说口语的变迁
其实从上面的论述中您也许已经发现,口语的变化是很难受人为控制的,因此在理论上口语既然是流行于大众之中的语言,就不可能太多的受文人的影响,所以他的变化应该是比较大的,而历朝历代的古文实际上都是由于文人刻意追求和先秦白话相似而产生的,所以韩愈的语言和先秦很相近(虽然我们可以在细微处发现韩愈的漏洞)
口语的变化最大的是语音,我们现在即使能够回到孔子的时代,但孔子和他的弟子讲学时说的话我们肯定一句话也听不懂,因为上古汉语的语音和现在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到唐宋时口语发音和现在的广东话和福建话就很相似了,所以日语发音和广东话总有点契合(当然,日语也在发展)
在词汇上有词义的变化和新词的产生
例如停车坐爱枫林晚中的坐在中古和近古有因为的意思,在上古却没有
在语法上的变化最小,有些古代汉语的语法特征随着成语保留了下来,比如宾语前置,我们现在说的唯某人马首是瞻,唯某人是问都是这样形成的
下面是我们现代汉语课笔记中的相关内容:
2.2.1. 现代汉语的概念和定义
(1) 古汉和现汉分期的不同说法:五四、鸦片战争、清末小说。
(2) 现汉的含义:
广义:包括普通话和各种方言。
狭义:专指普通话。
(3) 普通话是如何形成的——共同语形成的两个途径:
a. 自然形成,非强制性:
上海华和广东话对普通话的影响是非强制性的,是自然形成的。
b. 强制形成,人为规范:
在自然形成的基础上推广、规范。
(4) 共同语的表现形式:
a. 书面语b. 口语
二者形成的速度、过程不同,普通话有书面语和口语,且有各自不同的形成过程。
2.2.2. 现汉白话文的形成
白话文也是现汉中的书面语。
(1) 远古的白话文:
甲骨卜辞证明3000多年前与现在相似。
秦汉出现跨地域语言——雅言,即当时洛阳一带的语言,就是夏言。
书面语反映口语情况不一。《诗经》中的“风”忠实记录口语,具有民间口语色彩。《论语》记录孔子口语,反映当时的口语,而实际上先秦的人们也确实就是这么说,记录的一定是口语。
(2) 文白分离过程中的白话文:
汉魏以后,口语发生变化,当时的文人有意模仿先秦表达,形成与口语相去甚远的文言,文言的形成使汉语书面脱离了口语,文言在几千年间也一直占据了书面语的统治地位。
与文言书面语相对的是白话文书面语。南朝《世说新语》,遗留下来很多当时口语的痕迹,有很多口语的词汇、句子。六朝译佛经,在传播佛教教义的过程中需要向老百姓讲白话。唐五代后出现“变文”,属于一种说唱文学。古代佛教禅宗著作,在寺庙中讲经用,宣传佛教故事等,写的人文化水平不高,白话文痕迹很重,如《禅宗语录》、《祖堂集》等保留了很多的口语记载。宋朝朱子理学,讲学风盛行,《朱熹语录》极近口语。宋末元初,白话文成风,南宋末的话本(评书剧本)大部分通篇白话,而杂居散曲中保留很多口语。元末明初的长篇小说也不是文言,而是古白话,虽然颇具地方色彩,但都用北方话写,以北方口语作书面语的趋势产生,共同语书面语日趋完善,白话基本成型。
(3) 近代的“白话文运动”:
五四时期,陈独秀《新青年》发出口号: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最早刊登白话文《狂人日记》《伤逝》等,是为“白话文运动”。
1920年,民国教育部规定学校停止使用文言文教材,白话文终于取得文学语言(民族正统书面语)的统治地位,取代了文言文。
2.2.3. 现汉口语的形成
口语共同语的形成难以确定具体年代,但是一定比书面语晚。
在汉语史上,北方话在口语共同语上占优势地位。
(1) 雅言:
春秋战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人民言语不通,孔子讲学必须使用共同口语——雅言。
(2) 通语:
西汉杨雄《方言》记载周、汉各地口语、方言,书中也记录了一种“通语”,可见当时已有口头共同语的萌芽。
(3) 北京话对口头共同语形成的作用:
在口头共同语形成过程中北方话一直占优势地位,特别是1153年金定都北京以来,北京话逐渐成为最有影响的方言口语。
《中原音韵》记载古代都说北京话,“中原之音”为“天下通语”。
元末两本书《老左大》、《扑通事》是教外国人汉语的教材,采用的就是北京话。
北京话很快取得官话地位。官话不一定只有官吏才用。明朝科举规定都要说官话。
北京话向南方方言渗透,表现在:南方方言中出现一字两读、文白异读,白读指本地土话,文读指北京话。如:上海话中“大人”中的“大”白读,而“大学”中的“大”则文读。
(4) 清朝官话的推广:
清军南下将官话带到南方。在福建南平形成“官话岛”。
1728年雍正下令:官吏必须要掌握官话。雍正在闽、粤设正音书院。夹杂方言的官话称为“蓝青官话”。
(5) 清末,文字改革、口语统一、言文一致的要求迫切,有人开始搞拼音。
(6) 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
民国时,蔡元培发布“注音字母”,审定读音,当时还有关于采用京音还是国音(上海话)的争论,吴语中保留古汉语中入声和浊声母,若采用京音则要舍弃古语国粹。
注音字母、审定读音、国音争论和推广北京话,史称“国语运动”。
“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形成了普通话,台湾称之为“国语”,新加坡称之为“华语”。
古人为什么要把语言文字之学称之为“小学”呢?这也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小学”原本是指八岁至十四岁的幼童读书的学校。《大戴礼记·保傅》:“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人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卢辩注:“古者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人太学也。”汉崔定《四民月令》说:“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学,学五经;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篇章”是指《苍颉篇》之类的识字课本。因《苍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故以“篇章”指代这类字书。 在《汉书·艺文志》中,“小学”这个概念产生了新的意义,已由“学校”引申出“学科”的意思。《艺文志》说:“凡小学十家,三十五篇。”“小学”己成为一“家”之言,其内容全都是蒙童识字课本。《尔雅》、《小尔雅》这些书不算在“小学”家之类,其理由就是后来《隋书·经籍志》说的,“《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故附经籍之后。可见,汉代所说的“小学”实际上只限于文字学,它的具体内容包括解释文字的形体结构(六书,六体)、“通知古今文字”,以及“正读”字音等。
在《隋书·经籍志》中,“小学”这个概念又进一步扩大。其内容除字书之外,还包括训诂(如《说文》、《字林》等)、音韵等方面的著作,而《尔雅》、《小尔雅》、《方言》、《释名》等仍列入“经义”一类,不入“小学”之林。直到《旧唐书·经籍志》,才把《尔雅》等书列进“小学”一类,从此,“小学”的基本内容才确立下来。只不过在宋代,又有人把“小学”称之为“文字之学”。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说:
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衡纵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论体制之书,《说文》之类是也;论训诂之书,《尔雅》、《方言》之类是也,论音韵之书,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是也。三者虽各一家,其实皆小学之类。
晁公武把“小学”称之为“文字之学”,这说明古代的“小学”家并不把语言看做是自己研究的对象,即使在事实上研究的是语言问题,他们也是从文字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研究的,晁公武所说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就是指的字形(体制)、字义(训诂)、字音(音韵),即通常所说的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
由于古人认为“小学”就是“文字之学”,而且总是把“小学类”放在“经部”之中,因此,后人就产生了两种不正确的看法:
一、19世纪以前,中国还没有语言学;
二、“小学”是“经学”的附庸。古代的语言学不能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种看法是受西方的影响产生的,第二种看法是古已有之。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对。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语言学,这里有个标准问题。我们不应拿现代语言学的标准去衡量古代语言学,更不应该拿西方语言学的标准来硬套。我们应该从事实本身出发。我们的古人在东汉未年就已经能用二分法分析汉语的音节,从魏晋以后,就能很好地对汉语的声、韵、调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反映汉语实际语音系统的韵书(如六朝韵书以及《中原音韵》等),宋元时代又产生了声韵调相配合的等韵图,明清时代还产生了历史语音学,有的人己明确认识到:“今音不同唐音”,“唐音不同古音”,“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约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汉初为一时,汉武帝后泊汉未为一时,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汉语音韵学的发展,从总的趋势来说,是和汉语语音的实际发展情况相符合的。在词汇研究方面,公元一世纪就产生了《方言》,二世纪末又产生了《释名》,这些著作基本上是以当时的口头词汇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见,我们的古人无论是对汉语语音的研究,还是对汉语词汇的研究,都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属于语言学性质的。就是在今天,我们仍然把这种性质的研究划在语言学的范围之内。
古代语言学是否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呢?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应当确立这样一些原则:当我们衡量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独立的资格时,首先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对象,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方法,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科学体系,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成果。用这些原则来衡量一下,我们可以说,从汉代开始,语言学已经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了。《方言》、《说文》、《释名》这三大名著的产生,就是语言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的标志。我们说杨雄、许慎、刘熙是语言学家,大概多数人是会赞同的吧。汉以后,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人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也可以说得上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像李登、张揖、沈约、颜之推、陆法言、陆德明、颜师古、徐铉、徐锴、吴域、韩道昭、周德清、陈第、方以智、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江有诰、陈澧、俞越、孙诒让等人,都是重要的语言学家。他们在汉语、汉字研究方面,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当然,他们在观点上、方法上,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将会具体论述。另外,我们也应看到.古代的语言文字学和经学的关系的确非常密切,但古代哲学与经学的关系不是更为密切吗?就是史学、文学与经学的关系在先秦时代也不是那么分明的。《诗经》是道道地地的“经”,但它是不折不扣的文学作品,《书经》是道道地地的“经”,但又是不折不扣的历史著作。如果我们还跟古人一样,只在“经学”这个概念中兜圈子,不唯看不到语言学的独立存在,就连文史哲的独立存在也成问题了。就语言学的三个部门而言;也不可一概而论。训诂学与经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文字学次之,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于“经学”,但音韵学的产生和发展跟经学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如《切韵》系韵书和《中原音韵》系韵书的存在,难道不是独立的吗,能说这些著作都是经学的附庸吗!
有的人之所以不承认中国古代有语言学,不承认语言学的独立存在,一方面是受了“洋教条”或“土教条”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是对中国古代语言学没有作深入的研究。所以,我们要加强对语言学史的研究工作,要造就一批既懂得辩证法、唯物主义,又能贯通古今的语言学史工作者,要写出多种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来。围绕着这个任务,我们有下面一些工作要做:
用先进的理论作指导,对中国古代一些语言学名著重新进行整理;
要把古代语言学著作的系统、流派清理出来,从理论上建立起历史的联系,弄清中国语言学史的一些基本规律;
要开展断代语言学史的研究,如,“明代语言学史”、“清代语言学史”这样的题目,还从来没有人做过,做好这些题目,有利于对整个中国古代语言学生进行深透的研究;
对古代语言学著作中的一些常见的名词术语要进行一番彻底的研究,基本名词术语搞不请,我们就难以对古人的学术成果作出准确的评价;
要写好古代语言学家的评传。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等这些工作全都做好了之后,才能动手去写一部《中国语言学史》。而是认为:这些工作是究究中国语语言学史的人应当做的。有一定数量的人来从事这种研究工作,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水平才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有人问: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我谈点不成熟的意见: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每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应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继承并发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语言学史是整个文化史的一个部分,不仅研究汉语的人应了解汉语研究的历史,就是研究哲学史、文学艺术史的人,也应该对汉语研究的历史有一个起码的了解。
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虽然观点、方法都很不一样,但历史的经验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至少也应该把它放在跟介绍外来经验一样的位置上来对待。拿汉语史的研究来说,在很多方面就要利用古代语言学的成果,如果撇开这些成果,我们对汉语史的研究就会碰到很大的困难。
研究语言学史还要解决一个分期的问题。本师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将整个中国语言学史划分为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汉代到清代未年,第二阶段是从1899年别1949年。台湾省有位语言学家认为第二阶段(西学东渐的时期)的上限应提到明末。我个人认为这个意见不可取。明末至清代,某些西洋传教士和外交家,虽然也写了一些研究汉语的著作,中国的某些语言学家也接受了一些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但这并非主流,不应作为分期的根据。王力先生以《马氏文通》(1898年)作为两大阶段的分水岭是很正确的。因为《马氏文通》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它的出现,意味着古代语言学的终结,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不过,我认为古代语言学史和现代语言学史应该分开来写,各自独立成篇。本书名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就整个中国语言学史(古代的、现代的)而言,它只写了第一个大阶段的内容。在这一阶段中,我又分为六个时期,即:
先秦时期(?——公元前3世纪);
两汉时期(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初);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世纪——公元6世纪);
隋唐宋时期(公元6世纪末——公元13世纪);
元明时期(公元13世纪中叶——公元17世纪初);
清代(公元17世纪中叶一公元19世纪)。
古人在汉语研究中所造成的阶段性的特点,是我们进行分期的主要依据。
先秦时代以研究事物名称为特色;两汉以研究文字、词汇为特色,魏晋南北朝是汉语语音研究的开始阶段,是词义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阶段;隋唐宋是汉语语音研究趋向稳固、统一的阶段,在文字学、语义学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象样的成就,元明时代的语音研究以面向实际为主要特色;清代以研究古音古义为根本特色,这是古代语言学进行大总结的时期。
阶段的划分只能以反映某一时期的本质特征为原则,不可能照顾到各个方面,如拿等韵学的发展来说,应该是宋元算一个阶段,明清算一个阶段。而从全盘考虑,清代语言学不同于以往各代,特点很突出,应自成一段。我以为不必用绝对的观点来看待分期的问题,期与期之间不可能是一刀两断的,中间有过渡,有联系,不一致,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只要大致上合理,就不必斤斤计较了。
一本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究竟应当怎么个写法才好呢?这个问题我也仔细琢磨过。首先,我以为跟哲学史、文学史的写法应有所不同,如在语言学史中就无须用很大的篇幅去讲作者的世界观,去分析作品的思想性,也不必费很多的笔墨去谈社会背景,但语言学又跟文学、哲学、佛学、经学等有密切的联系,把这些联系恰如其分地揭示出来,对研究古代文化史也不无裨益。其次,怎么写跟为谁而写是分不开的,本书是为大学生和具有同等水平的语文工作者而写的,这些同志一般都学过“音韵学”“汉语史”这样一些课,所以我要力避重复,凡是在这些课程中已经解决得很透的问题,本书就少谈或不谈,如《广韵》是古代语言学史中第一流的名著,本书只有儿句话就交代过去了,就是基于以上的考虑。第三,我以为不论怎么个写法,似乎都应当把各个时期的语言文字学原著放在中心地位来评说,离开了原著,还有什么“史”可言呢?对广大读者来说,把原著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来分析评论,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样得到的“史”的知识,是具体的而不是空洞的,是联贯的而不是孤立的,何况有的原著一般读者已经很难看到了,不作必要的介绍就会“不知所云”。第四,作为一本“史”来说,应该综合当前研究的最高水平,应该是一个时代的智慧的结晶,不可能每一条材料都由著者发掘出来,也不可能每一个正确的论点都是著者的独创,著者有责任吸收各家之长。“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遗憾的是我有“取众白”的愿望,却缺乏精辨“黑”“白”的能力。且何者为“黑”,何者为“白”,也容许个人持不同的看法,至于这些看法是否正确,诚不敢自以为是。
平时里用白话文,写文章时用文言文!
古人说话是像我们一样还是文言文的形式?
其实从上面的论述中您也许已经发现,口语的变化是很难受人为控制的,因此在理论上口语既然是流行于大众之中的语言,就不可能太多的受文人的影响,所以他的变化应该是比较大的,而历朝历代的古文实际上都是由于文人刻意追求和先秦白话相似而产生的,所以韩愈的语言和先秦很相近(虽然我们可以在细微处发现韩愈的漏洞) 口语的变...
古人是用文言文对话还是像我们一样对话?
我觉得古人说话也是用文言文.只不过每朝每代的文言文都不同.比如我们现在看西汉的史记.根本看不懂 但是看北宋的资治通鉴,还能看懂点 文字是随着年代在变动的,我想清朝和民国时期语言方面应该可以互通的
古人真的就像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文言文那样说话吗?
并不是,从汉朝开始口语和书面语就是分离的。口语还是大白话,书面语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文言文。
古代人说话是像文言文一样,还是像我们现在的大白话?
其实,古代人的日常交流和我们现代人的说话方式是接近一致的,都是说的大白话,并非像史书经典上所记载的那样“文刍刍”,唯一差别就是我们现今的人说的是现代白话,古时候的人说的是古白话;那这样的说法有没有依据呢?有依据!有据可循的,最早可上溯至唐朝初期。在唐朝的《变文》和《唐传奇》中都...
古代时期古人说的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
后来都是使用文言文而古代的文言文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普通话一样,因此大多数的古代人在后续沟通的时候,都会选择用文言文沟通,而后来纸张也被发明了出来。不管是使用文言文还是使用白话文,都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古代人在使用文言文之后,也了解到了文言文的优势,因为我英文能够收最少的字,把...
古人说话是不是说文言文?如果不是,他们是怎么说话的?
第一个原因,文言文精简,不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现代人对于文言文的解释,就是以古代口语为基础的书面用语。我们所读过的文言文,大都是非常精简的,有时候能用几个字就不会用很大篇幅去描述。这是因为古代的造纸技术毕竟有限,谁会在珍贵的纸质文件上写上一堆废话?而且在造纸术大规模被应用之前,人们...
中国古代,当官的说话用文言文,老百姓说话用白话文吗?
古人说话写文章,用的都是文言文。只不过,说话用的多是口语;写文章用书面语多。官吏和老百姓说话用的都是一样的文言文。不过,普通老百姓一般不写文章。
古人说话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
古人说话是白话文,文言文一般用于写文章,比较难懂,一般的普通老百姓,显然是读不懂的。文言文只是相当于书面语言一样,它是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从春秋战国时期成型,到汉朝基本固定。文言文一开始就是与白话文分离的,文言文在表达上追求微言大义,要想实现表达微言大义的目的,在文字上就...
我们也一样的文言文
1. 古人说话是像我们一样还是文言文的形式 一方面是受了“洋教条”或“土教条”的束缚、流派清理出来。而是认为。 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虽然观点,某些西洋传教士和外交家,它只写了第一个大阶段的内容,魏晋南北朝是汉语语音研究的开始阶段,特点很突出,去分析作品的思想性,本书只有儿句话就...
中国古代人说的都是文言文吗?普通老百姓讲什么话?上朝说什么话,有方...
一、古人在先秦时期说的都是文言文,但后来文言文与口语逐渐分化,古人说的话也就变成了口语,与文言文逐渐脱节。普通老百姓也是这样说话。二、古代的官话与方言:1、中国历代官方语言有雅言、正音、官话、国语等不同的称呼,也是不同时期“普通话”的定义。官话可细分为八种次方言:北京官话、东北官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