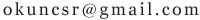第1个回答 2013-10-16
凌晨两三点,电话响了。我躺在床上,像棉絮一样摊着,四肢疲软,连手指头都懒得动一下。铃声“嘟嘟”地响了一阵,停了。是谁这么晚打电话呢?尽管我还没入睡,但也没人值得我在凌晨两三点听他的电话。很快,电话又响了,铃声在秋夜显得急促而尖锐。我拿起话筒,不耐烦地说:喂——我的声音疲乏而沙哑,但听上去很清醒。
电话那边停顿一下,声音惊惶而无力,仿佛要死抓住什么:“求求你,只要你不离开我,你要我怎么样都行——”这是一个女孩的声音,我一下子想不起她是谁。事实上,所有女孩子的声音在我听来都陌生而悦耳,我不熟悉任何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我没有女朋友,连异性朋友也没有。我在打工杂志社上班,我的同事有两位女人,都是年近四十的中年妇女,她们不可能发出如此清脆的声音。我笑了,如果是她们三更半夜打电话给我,那才匪夷所思呢。
电话那头仿佛在哀求:你可以过来吗?可以吗……凄惶而无助的声音,让我心生怜惜。我的声音变得柔和:你不要急,你慢慢说,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忙——我在斟酌着该怎么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子。我说,只是,你要找谁呢?你是在找我吗?电话那边戛然而止,黑暗中传来一阵啜泣,后来,电话机轻轻地挂上了。
我在黑暗睁大眼睛,愈发没有睡意了。我失眠由来已久。失眠的原因多种多样,譬如因孤寂而失眠,但孤寂是我的生活,我已经习惯。譬如因兴奋而睡不着,但生活就是如此平淡乏味,我除了读小学被校长在大会上表扬略感兴奋之外,已经有二十多年不知兴奋为何物了。一个人倘若置身于恶劣的环境之中,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会遭到扭曲,譬如被盟军关入大铁笼并让一盏发出强光的电灯没日没夜地照耀的老庞德,他的精神终于伴随着饱受折磨的身体垮了。白毛女在潮湿而漆黑的山洞生活了十几年,这就是旧社会使人变成鬼而新社会使鬼变成人的动人故事。只可怜那个如花似玉的喜儿无论是鬼是人都已饱受摧残,老了。
我失眠,是因为窗外的建筑工地在没日没夜地施工,那些巨大的噪声成了我生活中最突出的声音。每一个夜晚都被同一种噪声所笼罩,每一个夜晚都仿佛是前一个夜晚的复制,不会有什么不同。正如今夜,搅拌机发出的轰鸣声,电锯在切割钢筋发出的呼啸,像钉子不停地敲入着我的耳朵。我感到身体被尖厉的疼痛贯穿。
跟噪声作斗争,每一次都以我的失败而告终。我曾试过开音乐来抵挡噪声,音乐动听归动听,但无法抵挡噪声,无论是老帕还是恩雅的歌声,都无法跟搅拌机和电锯声相抗衡。我在同事的建议下买了一副橡皮耳塞,但效果不明显,噪声像穿过鱼网的水一样,毫无阻滞地流入我的耳朵。有时我睡不着就看书,又发觉没有什么书好看,更没有什么书值得在凌晨两三点爬起来看。我曾将门窗关得严严实实,但比戴耳塞还不如,除了几乎让我窒息,无济于事。我曾向那位年近四十的女同事学会了数绵羊催眠的方法。一个绵羊四条腿,四个绵羊八条腿——女同事说,这方法灵着呢,老公出差我就是靠这个入睡的。我试了几次,但当我数到一万六千条腿时(这是多少只绵羊?)我依然神清气爽。如果再数几个晚上,我肯定会成了速算的天才。后来我练起气功,以达到静心而入睡的目的。但我除了外面的噪声,还听到了体内风暴般的聒噪,我吓得不敢练了。
我放弃了一切努力。每天晚上,我洗澡后,就呆到床上去,等待那根本不属于我的睡眠。我一直要到凌晨四五点才因极度疲倦而迷迷糊糊地合上双眼。但我必须在七时让闹钟叫醒,并在八时之前回到办公室。老总是中国人,却长着一副外国资本家的嘴脸,恨不得榨干我们的每一滴血汗。
电话那边停顿一下,声音惊惶而无力,仿佛要死抓住什么:“求求你,只要你不离开我,你要我怎么样都行——”这是一个女孩的声音,我一下子想不起她是谁。事实上,所有女孩子的声音在我听来都陌生而悦耳,我不熟悉任何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我没有女朋友,连异性朋友也没有。我在打工杂志社上班,我的同事有两位女人,都是年近四十的中年妇女,她们不可能发出如此清脆的声音。我笑了,如果是她们三更半夜打电话给我,那才匪夷所思呢。
电话那头仿佛在哀求:你可以过来吗?可以吗……凄惶而无助的声音,让我心生怜惜。我的声音变得柔和:你不要急,你慢慢说,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忙——我在斟酌着该怎么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子。我说,只是,你要找谁呢?你是在找我吗?电话那边戛然而止,黑暗中传来一阵啜泣,后来,电话机轻轻地挂上了。
我在黑暗睁大眼睛,愈发没有睡意了。我失眠由来已久。失眠的原因多种多样,譬如因孤寂而失眠,但孤寂是我的生活,我已经习惯。譬如因兴奋而睡不着,但生活就是如此平淡乏味,我除了读小学被校长在大会上表扬略感兴奋之外,已经有二十多年不知兴奋为何物了。一个人倘若置身于恶劣的环境之中,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会遭到扭曲,譬如被盟军关入大铁笼并让一盏发出强光的电灯没日没夜地照耀的老庞德,他的精神终于伴随着饱受折磨的身体垮了。白毛女在潮湿而漆黑的山洞生活了十几年,这就是旧社会使人变成鬼而新社会使鬼变成人的动人故事。只可怜那个如花似玉的喜儿无论是鬼是人都已饱受摧残,老了。
我失眠,是因为窗外的建筑工地在没日没夜地施工,那些巨大的噪声成了我生活中最突出的声音。每一个夜晚都被同一种噪声所笼罩,每一个夜晚都仿佛是前一个夜晚的复制,不会有什么不同。正如今夜,搅拌机发出的轰鸣声,电锯在切割钢筋发出的呼啸,像钉子不停地敲入着我的耳朵。我感到身体被尖厉的疼痛贯穿。
跟噪声作斗争,每一次都以我的失败而告终。我曾试过开音乐来抵挡噪声,音乐动听归动听,但无法抵挡噪声,无论是老帕还是恩雅的歌声,都无法跟搅拌机和电锯声相抗衡。我在同事的建议下买了一副橡皮耳塞,但效果不明显,噪声像穿过鱼网的水一样,毫无阻滞地流入我的耳朵。有时我睡不着就看书,又发觉没有什么书好看,更没有什么书值得在凌晨两三点爬起来看。我曾将门窗关得严严实实,但比戴耳塞还不如,除了几乎让我窒息,无济于事。我曾向那位年近四十的女同事学会了数绵羊催眠的方法。一个绵羊四条腿,四个绵羊八条腿——女同事说,这方法灵着呢,老公出差我就是靠这个入睡的。我试了几次,但当我数到一万六千条腿时(这是多少只绵羊?)我依然神清气爽。如果再数几个晚上,我肯定会成了速算的天才。后来我练起气功,以达到静心而入睡的目的。但我除了外面的噪声,还听到了体内风暴般的聒噪,我吓得不敢练了。
我放弃了一切努力。每天晚上,我洗澡后,就呆到床上去,等待那根本不属于我的睡眠。我一直要到凌晨四五点才因极度疲倦而迷迷糊糊地合上双眼。但我必须在七时让闹钟叫醒,并在八时之前回到办公室。老总是中国人,却长着一副外国资本家的嘴脸,恨不得榨干我们的每一滴血汗。
第2个回答 2013-10-16
题目可以是 文学,无处不在
相似回答
大家正在搜